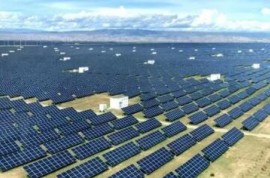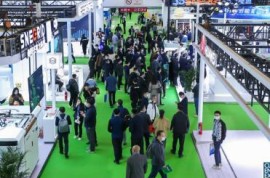過去十年,清潔能源發展速度超乎預期,為應對氣候變化、刺激經濟增長、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復合型解決方案。清潔能源、能效提升和綠色電力推廣,成為引領全球能源轉型的中堅力量,推動全球能源體系發生根本性變化。面對能源轉型重塑地緣格局帶來的契機與挑戰,中國作為最大的清潔能源生產國,應發揮自身結構性優勢,推動靈活多元的清潔能源外交,促進建構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共享、綠色安全的國際能源治理新秩序。
河北省平山縣崗南鎮李家莊村附近荒山上的光伏發電站 楊世堯 / 攝
全球綠色復蘇三大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萎縮,為了應對這一沖擊,各國政府積極制定經濟復蘇政策。然而,傳統的依賴化石能源消耗的經濟刺激,可能加劇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與健康風險。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IRENA)總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默拉指出,各國政府在制定后疫情時代經濟刺激和產業復蘇方案的過程中,需要融入清潔發展理念,加速向可持續性的脫碳經濟體和富有彈性的包容性社會轉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呼吁各國利用疫情后經濟復蘇的機會,攜手采取變革性綠色復蘇舉措,促進高質量綠色發展,構建更加清潔、公平、安全的世界。全球綠色復蘇態勢存在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全球綠色復蘇與碳中和目標緊密結合,成為新的大國共識。目前,包括中美歐在內的127個國家和地區,作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的重大承諾,支持綠色復蘇,控制全球升溫速度。2020年5月,歐盟公布總值達7500億歐元的復蘇計劃,推出一系列支持綠色轉型的措施,將落實《歐洲綠色協議》和《歐洲工業戰略》作為后疫情時代歐盟“化危為機、復蘇經濟的綠色動力”。2020年9月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倡議各國推動疫情后世界經濟“綠色復蘇”,匯聚起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合力。中國力爭于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美國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協定》后,將綠色經濟復興作為氣候政策的重心,重點關注與氣候相關的產業結構、市場需求、基礎設施投資、關鍵資源等,從而確保美國在2050年之前實現100%的清潔能源經濟和凈零排放。繼2015年《巴黎協定》簽署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后,推動全球綠色復蘇的大國共識,成為加速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引擎。
二是全球綠色復蘇中強調能源轉型的公平過渡和彈性適應。歐盟在綠色復蘇中形成新的《公平過渡機制》,提議籌集1000億歐元,以確保碳密集地區在進行工業和經濟轉型升級時實現“公平過渡”,并幫助疫情嚴重地區朝氣候中立目標發展轉型。拜登政府致力于將美國建設成為“氣候彈性和環境正義國家”:對清潔社區、建筑節能、彈性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開創性投資,制定氣候適應議程;注重少數族裔、低收入群體與工人的環境氣候權益。但是,歐美的“公平過渡”多局限于國內/地區內能源正義,忽視了全球能源轉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氣候適應能力提升、能源可獲性和公正轉型訴求。
三是綠色復蘇中能源轉型與數字化轉型的耦合度不斷提升。2019年,IRENA和國際能源署就提出了“智慧能源新業態”的理念,倡導加快能源與現代信息產業的融合發展,推進電力網、互聯網、通信網、光電網的多網融合互通,形成高效配置的智能化平臺。2020年3月,歐盟出臺《歐洲工業戰略》,明確提出綠色和數字雙重轉型理念,強調隨著波動性和分布式清潔能源占比的增加,數字化技術在保持電網穩定方面發揮的作用將更加關鍵。2020年12月,歐盟頒布《全球變局下的歐美新議程》,強調歐美需要通過綠色技術聯盟來領導可再生能源、電網儲能、電池、清潔氫以及碳捕獲等市場,通過對綠色技術、貿易和標準的主導來強化歐美綠色數字雙重轉型。
能源轉型重塑地緣格局
以石油、煤炭為代表的傳統化石能源生產鏈,都同特定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與之相比,可再生能源具有資源分布的廣譜性和生產的連續性等特點,其供給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風機、太陽能光板、儲能入網、綠色制氫等技術的革新。能源轉型正對全球地緣格局產生復雜而深遠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權力分配、國家間關系及地緣政治沖突。
英國擬 2030 年禁售汽柴油車,圖為倫敦一輛正在充電的電動汽車
第一,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被“再定位”且領導性資源發生變化。國家能源轉型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程度、國內清潔能源發展及其商業化水平。能源生產與分配的話語權正由資源國向資源與技術國家共同掌握轉變,未來甚至可能向技術國家傾斜。過去對地緣政治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化石能源出口國呈現出脆弱性,若不在新的能源時代調整經濟結構,其全球影響力將逐漸減弱。西方國家掌控的清潔能源知識產權與技術產業鏈,使其在能源轉型中仍具優勢,且可能進一步加劇南北差距,并惡化全球范圍內的能源正義問題。
第二,能源外交格局與國家間結盟態勢加速變化。伴隨著全球化石能源需求的下降,相關集團組織可能會松散瓦解。相反,基于能源轉型和清潔能源發展需要,能源外交出現綠色化轉向,各種新的國際合作機制、伙伴關系、政策網絡不斷涌現。西方清潔能源先驅國家(德國、荷蘭、丹麥、西班牙、美國等),在推進能源外交格局轉型初期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如德國因不滿國際能源署對化石能源的重視,于2004年推動了國際清潔能源大會(IRECS)、21世紀可再生能源政策網絡(REN21),2009年主導建構了IRENA。美國先后推進了亞太清潔發展與氣候伙伴關系(APP)、全球性清潔能源部長峰會(CEM)等機制的發展。這種外交轉型態勢不限于西方國家,如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峰會上,印度宣布成立國際太陽能聯盟(ISA),倡導熱帶地區國家加入,以此提升自身在太陽能領域的全球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
第三,綠色貿易和綠色金融新格局中的“共同治理”與“規則博弈”并存。一方面,清潔能源發展與電網互聯密不可分,增加綠電交易量的同時,增強了電網的抗波動性和穩定性。太陽能和風能等波動性可再生能源,需要靈活互聯的跨區域、跨國乃至跨洲的電力系統實時調峰網絡。這種跨境電力交易需要電力在管理良好和透明的市場中自由流動,也為區域合作帶來新的機遇,如IRENA的非洲清潔能源走廊(CEC)倡議被納入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非洲基礎設施發展計劃,旨在促進綠色能源市場的跨境電力貿易,并推進非洲各國的綠色融通與公平性低碳轉型。
另一方面,以綠色產業為重心的國際新經貿結構,逐漸成為未來支撐世界經濟的主流,與清潔能源技術相關的貿易爭端數量也有所增加。目前,世貿組織還未能解決清潔能源產品貿易因各國關稅、差別性補貼和不一致的技術標準所產生的阻礙問題,清潔能源的全球推廣、公平貿易和協調治理能力亟待加強,須尋求異于化石能源的國際治理架構。同時,隨著經濟貿易和金融投資格局的綠色轉向,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大國都已加大對綠色技術的研發投入。圍繞著綠色能源技術及知識產權、綠色供應鏈、碳金融市場、低碳法律配套等領域而進行的國際規則和標準博弈將日趨激烈。
塑造清潔能源時代的外交優勢
國際能源權力結構的變化,往往是國際體系重大結構性變遷的前提和條件,如英國和美國的霸權維系分別離不開來自煤炭和石油的能源支持。作為下一代能源體系的主導因素,清潔能源將在國際體系主導權爭奪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一國在能源轉型中的外交戰略優勢,有助于其在全球治理新秩序建構中發揮關鍵作用。中國自2009年超過德國和美國成為全球清潔能源生產首位大國,擁有綠色能源供給側的結構性優勢,為清潔能源外交的開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清潔能源外交的核心,是基于利益共享的原則,以綠色共贏的理念,推動構建靈活多樣的新型大國關系,并通過供應清潔能源的地區公共產品,提升中國外交布局中的綠色資源性權力,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
我國應把握清潔能源發展中的優勢,建立可持續的新型能源大國關系。可以就某個清潔能源合作議題建立制度化、常態化的溝通和協調機制,或將清潔能源議題同其他政治經濟議題進行良性互動聯系,借助其他平臺為大國磋商協調提供空間。同時,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清潔能源項目上,同其他大國開展第三方合作,探索建立大國清潔能源合作示范區,擴大合作共贏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要注重中國實踐與國際能源標準和機制對接,同時通過清潔能源合作和最優實踐推介來推廣中國標準。
可大力拓展基于清潔能源的“綠色南南合作”模式,推進綠色能源國際機制創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生態脆弱和氣候適應能力低的發展中國家,未充分開發清潔能源資源。而沿線大部分國家提出碳中和和清潔能源發展目標,為國際清潔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機。中國應立足于既有的區域和國際多邊機制,加強“APEC可持續能源中心”“東亞峰會清潔能源論壇”和“中國—東盟清潔能源能力建設計劃”等區域合作機制的協調,針對某一清潔能源領域推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長效性合作機制。同時,可以建構基于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社會部門共同參與的包容性清潔能源政策倡議網絡,大力推進以城市為載體的清潔能源合作伙伴網絡構建,實現四兩撥千斤式的多軌外交實踐。